
编者按:《新音乐产业观察》长期收集与音乐相关的创业故事。 欢迎提交或提供线索。
作者 | 男性
“今年先生存,先完成。” 广州一个小空间的老板阿星(王志兴饰)今年8月底还在等待演出市场的复苏。 地方就那么几个,理论上9月份旺季的时候人会很少。
两个月后,这个小空间11月的周末时段全部被订满。 Little Space是一个集Live House、录音室、咖啡厅、软饮店于一体的综合性音乐活动场所。 位于广州西关老城区荔湾湖畔。

“小空间”舞台
它于 2019 年 10 月开业,但仅仅两个月后就遭遇了 COVID-19 危机。 直到今年5月份,才慢慢恢复营业。 80后的阿星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在狭小的空间里,“都花光了”。
与新音乐空间老板相比,他在独立音乐圈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音响师、录音师和制作人。 从200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帮人制作专辑、探索混音开始,阿星的制作和混音经验已经有近20年了。 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社会学专业的顺德中年男孩,在朋友的推荐下,无意间去看了荔湾湖畔的古民居。 他受到启发,建造了广州为数不多的可容纳一到两百人观众的Livehouse之一,并建造了自己的Livehouse。 咖啡综合体融入其中。
生意才刚刚开始。 虽然花了很多积蓄,店里的生意刚刚恢复,但阿星对未来还是颇有信心的。 他再次四处奔波调音,用调音的收入来补充自己的小空间。
学习社会学的摇滚爱好者
在成为调音师、录音师、制作人和老板之前,阿星是一位摇滚爱好者。 2001年进入大学时,在顺德长大的阿星想去北方看看,于是考入了山东大学社会学专业。 原声吉他变成了电吉他。 学校的跨年晚会需要调音,没有人懂音响设备。 发烧友阿星只是顺着自己的感觉,在学校里找了一堆器材给他玩。 这是他接触调音的开始。
我大二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来了一位交换生,外号“李叔叔”。 他能填粤语歌词,自己弹唱。 他们在学校外面租了一个房间,根本不知道使用声卡进行录音制作。 他们利用电脑自带的声卡,插上耳机,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录音系统。 使用 Fruity Loops Studio 进行编曲。 阿星是听乐队长大的,有配器和配器的概念,所以他给李叔叔弹唱编了贝司和鼓,然后用Cool Edit软件录制。 李叔叔把专辑烧成实体并在网站上出售。 “这是我第一次做。”阿星说。
毕业后,阿星回到广州,在南方报业《21世纪经济报道》实习了两个月。 随后,他在 PCB(印刷电路板)生产巨头捷普公司担任仓库经理。 一年半了。
我八点上班,五点下班。 该工厂距离广州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平时的消遣是打篮球和看电影。 下班无聊的时候,阿星喜欢逛网络论坛。 他是“音频应用”的常客。 该论坛的创始人之一是因恶搞视频《包子杀人案》而出名的胡歌。 论坛充满了音频制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分享,以及音频爱好者之间的讨论。
曾经制作过专辑的阿星想通过论坛系统学习音乐制作知识和软硬件设备。 “当时国内没有专业系统的教材,基本上每天论坛上都聚集着这个行业的人,我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论坛看一看。”
他以前的音乐搭档李叔叔后来成为广州一所艺术学校的老师。 他热衷于组织和观看演出,不时在广州大学城组织音乐活动。 他请还在做仓库管理员的阿星来调音乐。 阿星说,刚毕业的时候,我对调音台还知之甚少,所以就靠感觉。
2007年,李叔叔带阿星去看了后来对阿星影响很大的乐队——沼泽乐队和秘密后院的演出。 看完演出后,阿星和乐队一起吃夜宵,从此他们就认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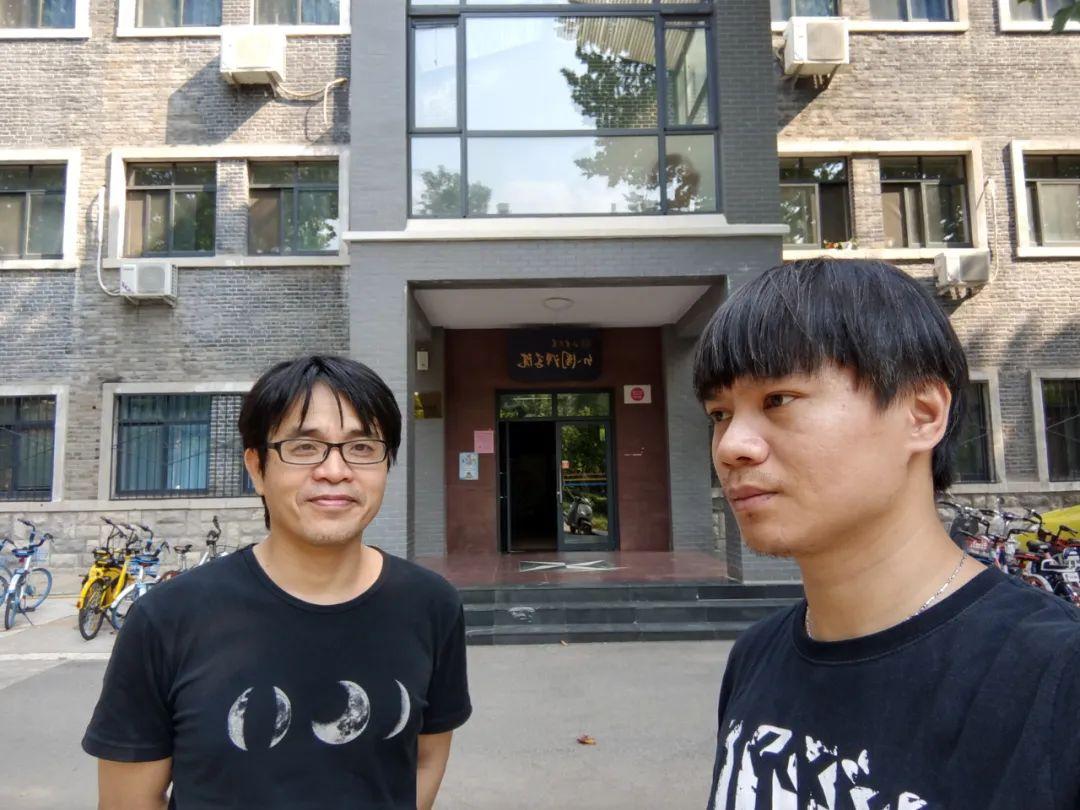
沼泽乐队巡演济南站期间,海亮陪同阿星参观了母校山东大学。

秘密后院成员的朋友开了一家叫精空间的酒吧,广州民间经常聚集,五条人也活跃在那里。 周末下班后,阿星时不时就会去精空间调音乐。
后来汶川地震后,广州音乐界推出了合辑。 秘密后院和沼泽乐队贡献的歌曲均由阿星录制。 马什成立了演出公司盛瑞,并举办了国内首届后摇滚音乐节,由阿星负责录音。 2008年下半年,跟随秘密后院前往厦门第六夜咖啡馆制作专辑《江湖边》。 这是他第一张正式制作的专辑。
永远在路上的调音师
当时国内乐队还没有伴奏调音师的概念,调音师也不专业。 调音通常是由乐队音乐家“盲目”完成的。 阿星正在帮忙调《秘后院》的性能。 演出结束后,他在咖啡馆天台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用两台电脑和两张声卡同时录制了《秘密后院》的新专辑。
此时,叛逆的李叔叔在学校格格不入。 2009年,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阿星也结束了朝九晚五的仓库管理员生活。 两人共同开设了铁力录音室。
但他们不擅长做生意,不愿意承担与音乐无关的商业工作。 从2009年到2014年的五年里,“我们两个人就被困在那里,录音室也没有成功。” - 这期间,他们制作了Secret Backyard的三张专辑、小雨乐队的第一张专辑、Black Ring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以及五条人和Swamp的几张小样。 “他们都是在给周围的一些乐队录音,而那个录音室并没有什么非常出名的作品。”
2009年,广州TU Space开业,这是广州当地最著名的livehouse。 铁力录音室不足以维持阿星的生活,他在途空间当了三年音响师以维持生计。 来自世界各地、各种音乐风格的音乐家来到这里演出,这给了阿星丰富的训练机会。 “我很幸运能够现场接触这些乐队。 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真正将调音视为一种技能。” 我的职业生涯从TU开始。”
2012年,沼泽乐队邀请阿星担任他们的巡演录音师,阿星在TU的频率减少了。 在一个场地待久了,他就熟悉了场地声场的调整,能够从容应对。 然而,当他走到外面时,每个场地的软硬条件都不同。 阿星开始研究场地的音响效果,“为什么不同的场地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去不同的场地?” 场馆是否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调整?”
在广州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音乐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阿星也开始涉足音乐节调音。 2012年底完成沼泽之旅后,阿星开始了他的环中国自行车之旅。
离开广州,阿星元旦抵达南京,一个半月后乘车前往北京。 阿星原本打算先在大城市待一段时间,赚点生活费,然后再继续上路。 北京的朋友听说蜀音乐在招人,就介绍阿星来应聘。

阿星在混音室工作
他负责蜀音乐录音室,半年的时间他大致掌握了北京中国摇滚音乐的生态环境。 在树音乐的六个月里,宋冬野在那里录制《安和桥北》,阿四在那里制作《人民广场吃炸鸡》,新裤子在那里录制张强的新专辑……
翻完几张专辑,帮徐佳莹和杨乃文调巡演后,阿星继续骑行。 “时不时地,我要连续上坡40、50公里。在成都骑行之后,我的骑行生涯就结束了。”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病,阿星膝盖受伤,近两年的骑行结束在成都。 2014年,阿星回到广州,偶尔也回到TU Space兼职主唱。 次年,前往广州YY文化传媒为女团1931选音。

阿星最后一次乘坐“西安至成都段”的自行车
阿星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自于他在YY工作的收入。 他还通过在 Midi 和 Strawberry 等大型音乐节上调音节省了一些钱。
表演的咖啡馆老板

阿星把这些年调音攒下来的积蓄都投入到了狭小的空间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建造这样一个实体的东西。” 通过朋友介绍,我了解到荔湾古城有意扶持创意产业项目。 阿星看了场地,对比了半年的计划,觉得这个livehouse可以实施。
他想打造一个纯粹的live house,“不要做酒吧,不要把喝酒放在一起。我跟乐队巡演的时候,最怕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live house在酒吧里,观众不是来看你的表演,但他们认为他们想买。” 买到票没关系,也不贵,也就几十块、一百块钱。 反正我进来喝酒就喝酒,你就是来招待我的……就算你不想开个空间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正好有二楼。 ,非常适合作为独立空间来分隔活动和饮料区域。 ”
阿星主修社会学。 他曾经痴迷于西方哲学,并养成了“虚无”的价值观:“我没有太多的观点,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为一件事生气。我只是能够用虚无来解释我的世界观”一种刻意不想形成主见的状态,“他觉得生活不需要留下太多波澜,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也不是人生规划。 刻意安排的结果。
阿星不喝酒,也不喜欢果茶。 他唯一的痴迷是将咖啡融入这个音乐空间。

“空间不大”的咖啡区
阿星在骑行时爱上了咖啡。 对他来说,咖啡没有提神作用,只是味道好而已。 读书时喝速溶咖啡,有了收入后开始喝现磨咖啡。 事实证明,咖啡也可以很有趣。 骑马时,他带了一套磨具。
从西安到成都,途经宝鸡太白山,太白山是秦岭山脉最高峰,海拔3767米。 2014年4月,气温在0℃左右徘徊,阿星将自行车存放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店里。 他是酒店里唯一的客人。 他带了两袋方便面和两袋速溶咖啡,准备进攻太白山顶。 第一天我们就睡在山腰上。 没想到第二天我们爬上去的时候,天气突然变了,下起了雪。
山上,他看着远处一头野熊的背影,以及不时出现的熊脚印。 场景就像是北欧森林。
登顶第二天早上醒来,阿星点燃了装满酒精的威士忌酒瓶,用水杯铲了一些雪,加热融化,泡了一杯咖啡。
狭小的空间里,在混音室或录音室工作之余,阿星偶尔会去饮料柜台泡几杯咖啡。
下一步是标签
正因为没有什么计划,阿星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空间狭小,定位于观众200人以下的演出,弥补了广州场馆狭小的短板。 “适合一些新乐队,也适合一些刚刚起步的乐队演出。这么小的空间,肯定不需要一线选手考虑,也不需要考虑。”二线球员。” 最近流行的乐队胡晓春和回春丹都是在狭小的空间里制作的。 场面火爆,一票难求。
但也有售票数为个位数的尴尬场面。 活跃于广州音乐圈多年的廖美娴,有小空间活动经验,负责管理场地的演出事务。 闹闹本来是作为咖啡师入队的,后来也做过跨行业的音响师,师从阿星。 承担部分调优工作。
进入狭小的空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两层长方形的饮料休闲区。 二楼还设有阳台和投影,实现聚会、讨论等多种功能。 咖啡厅的隔壁就是方正的表演场地。 走出去就到了后院,这里是观众和音乐家经常聊天或抽烟的地方。 进入后面的房子是低音量工作室。
阿星至今还没有主动宣传录音室,因为他不想接“乱七八糟”的工作。 他预计《乐队的夏天》将带动乐队产业,增加乐队对录音和制作作品的需求。 或许录音室的生意会逐渐好起来。
做了多年调音师,瓶颈主要来自于南北差异。 阿星的直观感受是,南方知名调音师不多,著名乐队也很少。 名人、著名乐队、著名调音师相辅相成,北方的调音师更容易因服务对象的知名度不断上升而出名。 “独立音乐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江浙等地。 起床。 广州地区非常薄弱。 广东的乐队要么规模小、自我推销,要么像沼泽地、秘密后院一样,不愿意迎合市场。 在这里成为一名音响工程师或制作独立音乐是相当困难的。 非常困难。”
最近,阿星想通过一个小空间成立一个厂牌,并签约一些乐队。 但这个想法仍处于起步阶段,他的时间都被伴随调音师的工作占据了。 “但这确实可以做到。”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受访者
-全文结束-